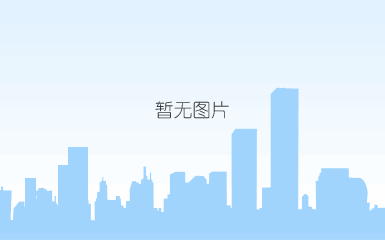外国音乐剧为什么那么难翻译
十几年来,翻译外国音乐戏剧的文本与歌词一直是我一个断断续续的工作。这些工作让我越来越多地认识到,音乐戏剧的翻译完全不同于话剧的翻译。特别是中文翻译,又有许多不同于其他语言的独特之处。
按常理来说,对于一般戏剧文本的翻译,照真实的字面意思翻译就可以了,重点是如何做到严复先生所提出的“信、达、雅”——“信为准确、达为通顺、雅为有美感”。“信、达、雅”三者在翻译时应视为一体,力求圆满,如能“形、音、义”三美具备,则是翻译的至美境界。但是对音乐戏剧的翻译来说,当音乐介入之后,新问题就来了。因为音乐剧的翻译必然要照顾到歌唱,由于歌唱的限制,我们往往又难以准确地按照外文的字面意思来翻译。有时,信了则不达,雅了则不信,当信达雅都有了,又无法演唱,很矛盾。为此,我们不得不在翻译时有所调整,有所取舍,也不得不在写意与写实之间寻求平衡。
事实上,在歌曲翻译上有所取舍,这在全世界都是普遍的做法。但多年翻译经历告诉我,用中文进行音乐戏剧的翻译,或许是各类语言中最难和最复杂的一类。为什么呢?大约有这样几个方面。
首先是汉语拼音的四声标准。我们都知道,中文是以声调的变化来进行词义区分的语言。通过网络查询,我得知,这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,只在汉藏语系(如越南、尼泊尔、印度)和非洲语系中才会较多地使用。而比如像英语,无论how are you还是hello,用不同声调来朗读,不会造成意思上的误解。日语、韩语、俄语、法语、德语也都是如此。这些占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语言种类,都属于“非声调语种”。这一类语种并非没有声调,只是他们的声调仅仅代表语气的变化,并不影响词义的理解。
而中文就比较特殊,四声的标准让语义变得千差万别。在四声声调的变化下,“出生”可以变成“畜生”、“土地”可以变成“徒弟”,“北京”可以变成“背景”,“互利”可以变成“狐狸”……还有一些词语,因为声调的变化,意思就更多,如“画家”、“ 花甲”、“画架”、“画夹”等等。 更多的情况,是产生了一些谁也听不懂的“词汇”,不知道在唱什么。
对于话剧文本的翻译,中文声调的变化不会是一个问题,甚至成为优势。因为用中文朗读,有“抑扬顿挫”的独特美感,这或许是“朗诵”作为一门艺术品类在中国流行的原因之一。好像在西方没有那么热衷于“朗诵”的。但是,当音乐进入后,所有声调的优势瞬间变成了劣势。因为前面所说的四声标准,让许多直译的文字无法演唱,或容易产生歧义。为此必须不断地调整和尝试,也许到最后能够找出一个相对妥帖的翻译,但无疑可选择的文字范围大大缩小了,而要翻译得传神、真切、易唱,就非常不容易。
因为声调的变化而在聆听歌曲时闹出笑话的,不用说外文翻译歌曲,中文歌曲中就有不少。比如: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西北风歌曲《信天游》中,“我低头,向山沟”,在音乐中,就会被听为“我的头,像山沟”;再比如歌曲《鲁冰花》中“夜夜想起妈妈的话”会被听成“爷爷想起妈妈的话”;张洪量的“你知道我在等你吗?”会听出“你知道我在等你妈?”等等,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。
你看,当音乐进入后,文字的选择就必须慎重了。中文原创歌曲尚且如此,根据外文的歌词翻译过来,受限无疑就更多了。
第二个弊端,是中文逻辑性弱、写意性强。这一特点也是语言界所普遍公认的。中文名词的时态、性别等,在单独拿出来朗读时是难以体现的,而中文句式的逻辑关系,也没有外文规整。也因为此,对于一句话的表达,中文无论在句型上还是文字的组合方式上,均多于外文很多,至少是多于英文。而像“枯藤老树昏鸦,小桥流水人家”这样的词句,包含着中国式的写意与韵律,同样也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。
中文的写意性强、逻辑性弱,反映在翻译上,就往往强于抒情,而弱于叙事。事实上这也是中文歌词过去一贯以来的整体特点——抒情强,叙事弱。我们很少能见到中文歌词中有如abba歌词里出现的清晰逻辑和故事感。中文歌词多数是讲情绪、不讲因果的。因此如果要选一些中国的歌曲串编成如《妈妈咪呀》这样类型的音乐戏剧,几乎没有可能。
最后一个弊端是押韵的方式。中文的歌词是习惯于押韵的,特别是押尾韵,这或许是从古代诗词传承下来的一种听觉习惯。一首歌,如果不压尾韵,往往不太舒服。虽然在现代的很多歌曲中,尾韵已不再严苛到必须句句押,甚至有个别歌曲,会刻意地不押尾韵以达到特殊效果,但对于绝大多数的歌曲,还是会遵守押尾韵的习惯。而在西方语言中是不强调押尾韵的,不论诗歌还是歌词。即便押,也是在句式中间押为多,而押头韵的概率也多于押尾韵。比如,pride and prejudice和sense and sensibility,就是押头韵的,而翻译成中文只能是《傲慢与偏见》和《理智与情感》,英文的韵律感就没有办法翻译出来了。
综上所述,当中文这样一种独特的语言,融入音乐戏剧之后,会面临“四声音调”、“写意与写实”、“押尾韵”等诸多天然障碍,让音乐戏剧的翻译比起一般的话剧翻译难度大大增加。
我们不妨回想一下,当我们观赏中文版音乐剧《妈妈咪呀》、《猫》、《q大道》的时候,是否有词义捕捉的困难?特别在歌唱速度较快的段落,是否无法完整听清楚演唱的内容?而翻译成中文的外国经典歌剧曾有过几部,为何后来无人传唱?哪怕是其中的经典咏叹调?而在观赏中文版音乐剧的时候,为什么演出时基本都有现场中文字幕?而我们在英、美、德、法等国家观看他们的音乐剧或歌剧时,从未见到过现场有本国语言的字幕显示。在日本和韩国等这些音乐剧本土化盛行的亚洲国家中,也从未见到本国语言的现场字幕。
为什么是这样呢?不能不说,拜中文“特色”所赐,音乐戏剧的翻译还真有些“先天不良”。
怎么解决这些问题?坦率讲,没有特别的办法,唯有把翻译做到更好。既然天生带着“镣铐”,只有把舞跳得更好看一些才行。如果还是从“信、达、雅”这三个方面来说的话,我有这样一些粗浅的体会。
首先,“信”,不只为了字面的“信”,也为了观众欣赏的“信”。
这如同金岳霖在其《知识论》一书中所说的“译意”,他说“所谓译意,就是把字句的意念上的意义,用不同的语言文字表达出来”。按照这一理论,像“to drink like a fish”应译为“牛饮”而非“鱼饮”;“god knows”应译为“天晓得”而非“上帝知道”;“a black sheep”应译为“害群之马”而非“害群之羊”,这样才符合汉文语意。
比如在翻译音乐剧《猫》时,全剧结束前,当魅力猫格利泽贝拉即将升入天堂,众多猫儿们唱到“up,up,up,up the russel hotel”(上、上、上、越过罗素饭店)时,如果你觉得“罗素饭店”观众并不了解,也难以翻译进入歌曲的话,可以把它翻译成类似“东方明珠”这样的建筑。因为t·s elliot在写这首诗时是1939年,当时罗素饭店还是伦敦最高的建筑。诗句的意思就是表达飞的高度很高。在不影响戏剧氛围的情况下,把它变成观赏者当地的最高建筑来转移概念,可谓一种方法。
“达”,不只为了通顺的“达”,也为了方便的“达”。
钱钟书先生曾说过,“未有不达而能信者也”。达,是为通顺,目的还是为了便于记住和理解。还是拿《猫》做例子,剧中有形形色色各种猫,每一只都有自己的名字,许多猫的名字又长又复杂,难以记住。比如“格利泽贝拉”、“史金波旋克斯”、“米斯托弗利”、“巴斯托夫·琼斯”、“老杜特洛诺米”等,那么在翻译时为了方便,我便根据每一只猫的特征取了大大小小很多名字,如“火车猫”、“富贵猫”、“魅力猫”、“魔术猫”等,这样每一只猫,就能方便地被观众记住。
“雅”,不只为了美感的“雅”,也为了歌唱的“雅”。
如何在保证基本词义的前提下,做到“雅”,是音乐戏剧翻译中最难的地方。因为需要演唱,因此译者除了需要优秀的中外文功底之外,还要有良好的乐感。翻译出来的文字,不论看上去有多美,先得经得起自己歌唱的考验,否则也是白搭。而为了歌唱这一最低也是最高的标准,类似“置换句序”、“词义增减”、“字意转化”、“转换概念”等手法,往往都是必须的。
以上这些翻译例证,并非唯一方案。所谓“文无第一,武无第二”。好的翻译,必然也是各有各的好,甚至“没有最好,只有更好”。综合来说,音乐戏剧翻译的重点是歌词的翻译。好的译者,必然要是一个好词人。而更重要的是,音乐戏剧的译者必须具有良好的乐感,能识谱,最好是唱歌也具有一定水准,这样才能够指导和纠正演员的中文演唱。有时同一首歌曲的翻译,被如何演唱出来,也会有不小的差异。如果译者可以乘着歌声的翅膀,发挥自己的想象力,表达出原文背后的真实意图和情感,那么也许,我们也可以翻译出和原文一样贴切的歌词来。虽然,这看上去是多么的不容易。